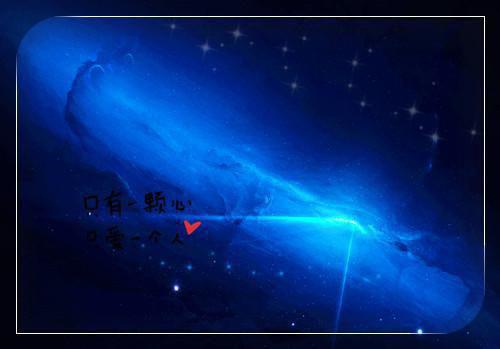杀了真千金后,我疯了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《杀了真千金后,我疯了》全文
|
命人烫伤我拉小提琴的手,将我绑到仓库,凌辱致死。 重活一世,我先发制人,设计将她溺死在泳池里。 葬礼上,看到她的骨灰盒即将埋到墓地里,我却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。 反而心底弥漫着无尽的哀伤。 我好像忘记了很重要的事情。
“不要” 在骨灰盒即将放入墓地时,我疯了一样冲上去。 陵墓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,骨灰盒脱离了他的掌控。 我快速接住掉落的骨灰盒,如获至宝一样把它抱在怀里。 “还好没事儿” 我低头喃喃自语。 还不待我再仔细检查,我的左手被人抓住,尔后脸上是一阵剧痛传到我的神经。 “赵瑾,你闹够了没有,你就这么容不下你姐姐吗?就不能让她安生的走吗?” 我爸劈头盖脸打了我一巴掌,看到他怒不可遏的表情,再低头看下我手中的骨灰盒。 我一脸茫然。 我在干什么,我怎么会上来抢赵楚涵的骨灰。 我的养母先一步上前,“你消消火,不要在楚楚的面前动气,我不希望大家在楚楚面前闹的那么难堪。” 养母眼睛红肿的不能看,连声音也是沙哑不堪。 我想开口叫声妈,但对上的确实她憎恨的眼神。 我认得,那是恨不得让我去死的眼神。 为什么?就算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,你也养了我十几年,为什么你会这么看我?为什么没有人爱我? 对,都是因为赵楚涵,她霸占了我的亲生父母,让养父养母也对我厌恶。 凭什么因为嫉妒心就要烫伤我的手,凭什么要让那些绑匪侮辱我,对,她该去死,去死。 看着手中白色的骨灰盒,我生出了一个邪恶的想法。 如果我把赵楚涵的骨灰都倒掉呢?那该多有意思。 我握着骨灰盒的手攥紧,欲把它举到头顶,可手却在不断颤抖。 就在我犹豫之间,骨灰盒被人抢了去。傅闻州将它再次交给了工作人员。 “你干什么?” 我很想冲他发火,可抬起头却看到宾客都在指着我窃窃私语。 “看吧,她真的疯了,本来我还不信,真的是个疯子” “谁能想到她会变成这样,听说她谁都记不得了,还一个劲儿叫傅闻州姐夫,也是个可怜人” 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怜悯,仿若看着一个精神病。 他们在说什么?为什么我听不懂。 我想上前去问清楚,可傅闻州却紧紧将我箍在怀里,他把我裹紧他的风衣中,捂住我的耳朵。 “阿瑾,没事儿,没事儿” 他声色哽咽地抚摸着我的发丝。 抬头看着赵楚涵的这个未婚夫,我觉得很恶心。 前世那么爱赵楚涵的傅闻州,这世我只是撩开了裙子就轻而易举的爬上了他的床。赵楚涵才死了几天,就和我滚到床上翻云覆雨。 什么十几年的青梅竹马,还不是勾勾手就到我的手边。 赵楚涵的骨灰盒还是放入了陵墓,这个作恶多端的女人终于死了,我真该放声大笑,可为什么我的心只感到痛,痛到我想嚎哭。 天空逐渐下起蒙蒙细雨,我伸手擦去眼角的水渍,不知道这到底是雨水还是我的泪水。 “唔” “阿瑾,你别这样。” 傅闻州轻轻地拿下我环绕他脖领的手臂。 可我偏不死心,再次缠上他,继续加深这个吻。 刚一进玄关,我就把他按在墙上亲,他的身体也在诉说着他的情欲。可理智还是战胜了欲望。 “阿瑾,你冷静点,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?” 干什么?当然是做男女欢爱之事啊。 这个曾经欺负我的男人,他到底在装什么? 我永远忘不了他为了帮赵楚涵出头,指挥混混撕开我衣服的那种不屑与玩味。 当初我拖着破烂不堪的身子,毫无尊严的跪在他的脚下让他放我一马,可换来的是什么呢?是更多的欺辱与疼痛。 赵楚涵死了,可这些帮凶都还在。 他不是爱赵楚涵如命吗,他不是嘲讽我是个被人不要的破鞋吗,那我也让他尝尝爱上人却被丢弃的感觉。 我不听傅闻州的警告,反而更得寸进尺,我把他的衬衣撕开了个口子,露出些许薄肌。 傅闻州被我攻破了底线,他横抱着我快速上楼。 月上中挂,月光倾泻在被子上。 屋内一片旖旎。 “把药吃了吧。” 傅闻州向往常一样递给我药,重生归来后,我总会梦见前世的场景,那些痛苦经历折磨的我难以入睡,只有吃下安眠药才能睡着。 可是今日,我不想吃。 “我不吃” 傅闻州皱了皱眉,“不吃药,病怎么好?” 病病病,又是病,从葬礼到现在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说我有病。 我任性地把枕头甩向傅闻州,“我没有病,我只是失眠,我没有病,我今天能睡得着,我不用吃药。” 枕头甩在脸上,可傅闻州还是保持着一手拿水,一手拿药的姿态不动。 “好好好,你没病,但你今晚再失眠怎么办?乖乖把药吃了吧。” 仅仅一个失眠,为什么傅闻州会紧抓着我不放。 这真的是失眠药吗? 我接过傅闻州递来的安眠药,当着他的面将瓶子里的药全部倒在地上。 药和地面接触,发出轻微的响声。 “阿瑾,你!” 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傅闻州没反应过来,他快速放下杯子,一个瞬身来到我的脚下,跪着捡药。 我看着他一粒一粒的把药拾到瓶子里。 这副屈辱的样子和我当初好像,可是这还不够。 在傅闻州捡完后,我又将瓶子踢翻。 把那杯水从他的头上倒下去,水顺着发丝溅到地上,最后一点,我全倒在他捡药的手上。 水流渍了一地,把白色的药丸溶解成粉末。 “啊”热水烫在傅闻州的左手上,让他啧出声。 我很想问他,疼吗,疼就对了,当年赵楚涵用100度滚烫的热水毁掉我的双手时,可比这疼多了。 可傅闻州什么也没说,只是默默的收拾这一切,然后出去了。 空荡的房间里又只有我一人。 这一晚,我确实如傅闻州所说的失眠了。 我又梦到了高中的事,女孩儿被一群人围着,她们疯狂大笑,为首穿红色外套的学生是最得意的,她不顾女孩的泪水,硬是把女孩儿的手放入滚烫沸水的沸水中。 持续一分钟的欺辱,尽是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声,而那群人笑的是那样猖狂。 那群人走了,只有女孩蜷缩在角落里哭泣。 多次午夜梦回时我都会看到那个女孩,可我从看不到她的脸。 这次她终于抬起了头,那是我的??是赵楚涵的脸。 为什么会是赵楚涵? 不该是我吗? 是我被赵楚涵毁了手,我才是受害人。 我伸手去揉捏那女孩的脸,可任凭我怎么揉捏,那就是赵楚涵的脸。 既然被欺负的人是赵楚涵,那我又是谁? 我缓缓向镜子里看去,镜子砰地一声四分五裂,破碎的镜片映出我的脸,我穿着红色外套,手里拿着刚倒完热水的水壶,得意的笑着。 “啊——啊——”我吓得拿起水壶砸向镜子,细碎的镜子还是没掉落,镜中又映照出另一个女人面孔,女人披散着头发看着我。 “赵瑾”身后传来诡异的声音叫我的名字。 我向后看去,蜷缩着的赵楚涵早已不在。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红衣女鬼。 女鬼突然间抬起头,我看到她眼睛流出血泪,脸上全是碎片的抓痕,巨大的玻璃片扎投她的心脏,她的四肢。 “赵瑾,你害的我好苦啊。” 我怎么会认不出来这个女鬼呢,她是被我杀死的赵楚涵。 赵楚涵不断呢喃着,左手不断握紧玻璃碎片,那玻璃扎进她的掌心中,血液顺着玻璃流了下来。 “别过来,别过来。”我害怕的嘶吼出声。 “你别过来。” 这是我弄死赵楚涵后,第一次在梦里见到她。 我害怕,我真的害怕,杀人的恐慌感淹没了我的理智。 赵楚涵没听,反而开始狂笑着走向我。 “啊啊啊——”我不顾一切的冲了出去。 用尽最大的力气去下楼梯。 一中的教学楼只有五层,可我却怎么也看不到尽头。 赵楚涵一直跟在我身后,她的笑声回荡在空荡的走廊中,诡异,恐怖。 最终我筋疲力尽的停了下来,还没喘完气,赵楚涵那张放大的面容就出现在我前面。 “啊——”我吓得倒在地上。 赵楚涵压在我身上,让我挣脱不开。 她把那块玻璃碎片抵在我的脖子上,用那嘶哑的声音喊我的名字,“赵瑾,你知道摔下楼被玻璃碎片贯穿身体是什么感觉吗?” “你知道玻璃划破心脏有多疼吗?你知道剩下一口气却动弹不得,只能任凭血液流干至死的感觉吗?” 她抓着我的衣领,笑得更加癫狂。 “不,你不知道,你什么也不知道,你夺走了我的父母,我才是赵家的亲生女儿,你这个鸠占鹊巢的女人,你毁了我的手,你毁了我的一切,凭什么你还那么幸福,今天我也让你感受到我死时候有多么痛。” “该死的贱女人,去死——去死——” 她的面容越来越狰狞,握着玻璃片的手猛然抬起,那锋利的刀刃向我袭来。 “啊——” 我从梦中惊醒,大口喘着粗气。 环顾四周,是傅闻州的家。 我向后看,枕头被我的汗水浸湿,黏糊的汗液在后背滑落。 傅闻州不在,斜对面的书房亮着些许微光。 我从门缝中看见傅闻州颓废的坐在椅子上抽着烟,握着纸张的手愈发收紧。 烟雾氤氲,我看不到他的表情。 突然间他起身,拨开电话,走到窗户边。 “李医生,是我。” “您能抽空来一趟别苑吗,我爱人她情绪不稳定,把药毁了,您能不能再开些药。” 对面的人一直在说话,傅闻州只是静静听着。 在挂掉电话前,傅闻州看了看窗外那棵梧桐树,“她记不记得我没关系,我只要她好好活着,就算记不起我,我也能让她爱上我。她只是病了而已。” “她是我未来的妻子,就算她一辈子也好不起来,我也会陪她一辈子。” 我又回到了房间,关上灯,重新睡觉。 这次,我没再做梦,睡得很安稳。 我感到有人在抱着我,他的手放在我的腰间,宽大温暖。 我起床后,傅闻州已经做好了早餐。 该说不说,傅闻州这大少爷的手艺是真不错,做的都是我爱吃的。 和他在一起的这几天,就没踩过雷,我和赵楚涵的口味截然不同,他还能把饭做到我的心尖上。 “你今天怎么不去上班。” 我扒拉着米饭问他。 傅闻州擦掉我嘴边残留的米粒,温柔的笑着“等一下再走,有些事情要处理。” “叮咚——” 门铃响了起来,门外站着一个穿着白色大衣的男人。 我知道傅闻州要处理什么事儿了,他要处理我。 男人温吞的向我自我介绍,让我叫他李医生就行。 “赵小姐,你不要紧张,我只是简单的给你做下检查,放松下就行。”李医生问我这几天有没有什么不舒服,记忆力如何。 “都挺好的,没什么不舒服,我记忆力挺不错,昨天看的小说还没忘。” 李医生耐心的倾听者。 傅闻州从开始到现在就坐在我旁边,他把手放在我的腰间,仔细地听着我和李医生的交谈。 李医生走之前把傅闻州叫到一旁,他们俩说了很多,我看到李医生从包里拿出一瓶药交给傅闻州。 “阿瑾,吃药了。” 睡觉前,傅闻州又拿着那瓶安眠药站在床头。 我一把把药抢了过来,光脚下地,把药尽数倾斜到窗外。 “阿瑾,你干什么?你知道那些药有多重要吗?” 傅闻州的手掌使劲儿捏着我的肩膀,那力道强的快要把我捏碎。 这是我第一次见傅闻州这般生气,哪怕是赵楚涵被医生宣布死讯那天他也没这么发怒过。 我甩开他的双手,站到床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 “我当然知道我在干什么?那根本不是什么安眠药,那是治疗精神病的药物。你以为我没听到吗?李医生和你说我是精神病,你们都说我是精神病,可我很正常,我没有。” 所有人都骂我是精神病,他们觉得我疯了,可我没疯,我记得那些疼痛,记得碎片划伤进皮肤的声音。 我只是不想沦落到和前世一样的下场,我不想屈辱的死去,我不想看到仇人快活。 我只是变得叛逆,变得不听话,可是所有人都骂我是疯子。 难道只有做个乖乖女才是正常人吗? 不正常的是他们,该死的也是他们。 对,傅闻州也该死,这个害我凌辱致死的人,他就该和赵楚涵一起下地狱。 我走到床台前,拿起床柜上的玻璃杯,摔向傅闻州。 玻璃杯砸到他的额角,血液随着散出来的温水留了下来。 看着傅闻州被我伤的模样,我笑得愈发开心。 傅老爷子来的时候,我没有下去。 我在二楼看着傅老爷子拄着拐杖骂傅闻州。 “你看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了,那个女人疯了,你也疯了吗?” “你看清楚,她早就不是以前的赵瑾了,她就是个精神病,把一个精神病人放在家里,你都不害怕她会做出什么事情吗?” “今天她敢打你,明天她就敢在你睡着的时候杀了你。” “为了这么个女人,你连公司都不管了,你还知道自己姓什么吗?难道你真要搭上自己一辈子。” 傅闻州推开傅老爷子的手。 “她只是病了,只要好好治疗就能好的。” “如果好不了,那我就管她一辈子。她是我的未婚妻,也是我未来的妻子。我永远不会放弃他。” 傅老爷子被气的倒在沙发上,捂着胸口。 好一会儿才缓过来,他大力的敲着拐杖。 “造孽啊,真是造孽啊,我傅家竟然出了个大情种。” 傅老爷子气愤的离开了。 也是那天起,傅闻州再也没逼我吃药。 他让我放下手机里的小说,带我去看青海的赛里木湖,北极的极光。 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,快乐的都快让我忘了前世他对我做的事儿。 刚从国外旅游回来的第一天,傅闻州就被老爷子叫去傅宅。 而别苑也来了个不速之客。 丁晓语,我的高中同学,高中时就是风云人物,仗着家境殷实,处处旷课,在社会上交到不少哥哥。 从高中开始她就爱穿红色,哪怕是春暖花开的季节,她都要穿件红色外套。 而今她穿着红色的高跟鞋,红色的大衣,抹着红色的口红站在门口,手里牵着一个两岁多的孩童。 我把她引进门,她也不客气,反客为主,自在的坐在沙发上和我聊天。 她喋喋不休的讲着自己高中后的经历,讲她现在过得多么滋润,什么也不用管,就在家里做个富太太。 我很少搭腔,只是静静的听着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太多了,她的语速慢了下来,慢慢地靠近我,“你记不记得去年的10.10发生了什么吗?” 去年的10.10有什么问题吗?我皱了皱眉头。 丁晓语连忙摆了摆手,“你别紧张,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 “去年的10.10,我当然是在......” 我努力去回想,可只要一想我想我的头就开始剧烈的疼,疼得我视线变得模模糊糊,整个房子都在天旋地转。 我脑中闪出很多画面,我衣褛不堪的跪在我爸面前,声嘶力竭的让他放过我,可他还是过来扒着我的衣服。然后是玻璃破碎,碎片穿透赵楚涵的身子,她嘴里不断吐鲜血,血液浸染了她身下的草坪。 好疼,真的好疼。 我努力去寻找支点,丁晓语早就不在。 “滚,滚出我的家。” 我听到傅闻州的怒吼声,循声望去,丁晓语牵着孩子,缩着头灰溜溜的走了。 我向玄关的方向望去,脑子愈发疼的厉害。 在倒下看到的最后一眼,是傅闻州飞奔向我的场景。 再次睁眼是卧室的天花板。 傅闻州左手撑着头,坐在我的床边。 “你醒了。”他起身将枕头立起来,好让我能依仗着。 “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吗?” 我摇了摇头。 “你爷爷找你有什么事儿吗?” 傅闻州告诉我,我爸被查了。 “你爸负责建造的游乐场出了命案,可能要进监狱。” 我爸庭审那天,我也去了,以证人的身份。 这些年他为了中标,多次贿赂公职人员,在建造过程中偷工减料。 我站在证人一方,举起手中的日记本。 “这里记录着赵春这些年来行贿的所有过程。” “他在饭局上通过送钱、送美人的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。” 被告席上的我爸沧桑了不少,曾经那个最注重形象的父亲,此刻以最邋遢的样子站在这里。 从审判开始,我爸就一直低着头,让人看不清他的面容。 如果能抬头,那一定是痛苦、懊恼的表情。 在我陈述完后,我爸终于抬起了头,他一定很.......他在笑?为什么在笑? 我爸的辩护律师此刻站了起来。 他拿着一张纸面向法官。 “这是赵瑾小姐的精神病病例,从去年11月开始,她就被确诊精神病。” “按照我国法律,精神病人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之人,那么她的证词也无效。” “这些所谓的行贿过程很有可能是伪造的,不能成为证词。” 他在说什么?什么伪造的?这是我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啊! 赵春逼着我去给那些老男人敬酒,纵容那些人在我身上揩油,我都是记得的,他怎么能说那些是伪造的。 “你才是伪造的,这些是我亲手写出来的,所有的行贿金额都能对得上去。” “你才是精神病,你全家都是精神病。” “啊——”我拿起那本笔记本就向他砸去,又觉得不够,转头要离开打他。 法警按住我的双手,押着我离开庭审会场。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法院大门的,出大门那一刻,媒体的摄像头就怼着我。 那些记者咄咄逼人“赵小姐,您作为赵家的养女,今天亲自作证举报你的养父,请问你是什么心情?” 傅闻州抱着我的双手愈发用力,他将我的头埋在怀里。 “让开,让开。” 可记者还是不放过我,“赵小姐,当年赵楚涵坠楼而亡的事情真的是个意外吗?” 我的头又开始疼了,我看不清楚这些人的面孔,只能看到他们的嘴一张一合。 养女?坠楼而亡? 他们在说什么?为什么我听不懂? 赵家的养女不是赵楚涵吗?赵楚涵不是被我设计在游泳池里溺死的吗?可怎么都说她是坠楼而亡。 疼,脑袋真的好疼,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,就连傅闻州拽着记者怒吼的声音我也听不到了。 |